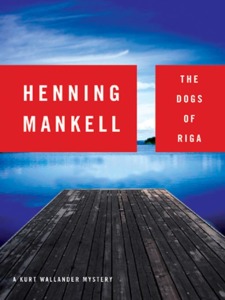(2005 年 8 月 18-23 日)
一、
飛天賓館的住宿規則:
在櫃台付房錢(160?),加押金 100 元,領一張加了護背的小紙卡,以及早餐券。
到了房間所在樓層,將小紙卡交給電梯口的樓層管理員(晚上是胖大娘,白天是瘦女士;年紀接近,差別在於穿著)。管理員負責開房門(但那晚那間空房的門沒鎖),並且交給客人電視遙控器。
房門是喇叭鎖,鑰匙不交給客人。客人外出時得自行鎖門,回來後找管理員開門。
退房時,先告知管理員。管理員檢查了房間,才發還小紙卡。拿小紙卡到櫃台退押金。
有冷氣。窗子分內外兩層,可能是冬天防寒,同時也隔音(窗外是火車站前廣場)。枕頭套、床罩感覺上都睡過人(所以當晚就用了防蚊貼片)。電視都是國內頻道,每換一個頻道沒多久就跳出一個有字的紅色圖案蓋在畫面上(防客人看太久?)。
二、
大同賓館周圍有圍牆。走進大門,左手邊是餐廳、會議廳,正前方幾十公尺外是賓館主建築,其他空間是沒什麼花草樹木的庭園。
住宿沒什麼特別規則。房間不小,天花板挺高,床鋪也乾淨。不過,除了美金換人民幣挺方便外,沒發現這賓館有什麼特色。
三、
太原的并州飯店在大路交口,沒有圍牆,兩棟主建築橫著排開;一樓進門後,還沒走到櫃台,兩側便是長長的客房過道。
住的應該算是套間,臥室與客廳間有門。客廳沙發大而軟,坐下就不想起身。厚窗簾外面是五一廣場南側的眾多人車。
櫃台人員動作不俐落。附設書店的書超乎意料的好。住房附的早餐非常豐盛。
四、
一得客棧在平遙沙巷街。稱為「街」,感覺上是條巷子,走在裡面,靠牆比過門的機會多。出了客棧向右轉,二、三十公尺外的西大街,才真的像條街(說「路」也行)。
可以接送客人——臨走那天清晨早起,就看到老闆娘的先生(?)去火車站接了四個從西安搭夜車過來的年輕外國男女(學生?)。房間乾淨,被褥舒服。而且,好安靜。
老闆娘一直為了停電致歉。但是夜裡點著蠟燭,在院子裡納涼,吃蔥油餅,配啤酒,真是享受!
五、
大同是歷史名城。但若不是進了下華嚴寺(大同市博物館),我其實沒看到多少「歷史」。
《藏羚羊山西》的大同市地圖上畫出了「城」,而且有南北兩圈。因此,出發前,以為到大同可以住在「城裡」。車站、飛天賓館在市區北端,大同賓館在市區南端,但搭車途中東張西望,都沒看到「城」。離開前的中午,朝大同賓館走的時候,才終於看到「城跡」。
當然這次沒有看到大同的全貌。走過的無非賓館附近,以及從大同賓館到華嚴寺那一段。不容易想像柏油路面的城市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灰塵。很難相信怎麼有像驢子那麼乖順的動物。
六、
大同是煤的城市,太原是鐵的城市。巴士下大運高速之後,抵達火車站前的迎澤大街之前,開過了市區東北角很大一片與「太鋼」有關的地段。
若不算從平遙回來、準備搭機到上海的那段時間,待在太原的時間不到 24 小時。雖然只在并州飯店附近走動,但感覺上太原顯然比大同大上許多——路寬屋高,車多人多。
在解放路上聽到《老鼠愛大米》。台灣人蠢得真是夠了。
在潦草的柳巷(其實是條「街」)吃到「肉夾饃」。其實是「饃」夾著「肉」,碎碎的滷豬肉。饃不錯,肉很鹹,總成績一般。比較有趣的是:得先買票,憑票領饃。
柳巷有不少攤子賣「大連魷魚」,和台灣的「烤魷魚」差不多做法,一串一串賣,但看到烤的都是鬚鬚。(魷魚是海產,山西是內陸,所以鬚鬚也算新鮮東西?)
在柳巷發現一家電影院。因為《太行山上》的海報而走進去,被一位大娘厲聲喝住:「你找誰!」,回答「我看海報」之後逛了一兩分鐘,離開時確定有些小房間放錄像,不確定到底演不演電影。
七、
在平遙火車站下巴士時是午後,第三天上巴士時是早晨,大約待了兩整天減一個早上,比在北京的時間短,但感覺上卻較長。或許因為,除了初到時自西門外搭機器三輪車到客棧、離開時從客棧搭轎車到火車站之外,都靠腳移動;久與土地接觸,距離便莫名其妙地換了單位,成為時間。(天長地久?)
平遙是這次旅途中我最放鬆的地方。雖然「兩整天減一個早上」的時間,有整整一天多沒電,第一夜夜半乍醒且以為看到了鬼——沒眼鏡沒燈沒蠟燭,瞪大眼睛再看,似乎是晾在房門口白牆上的外衣,便倒頭續睡;事實如何,不知道。
平遙是晉中市(地級市)底下的市轄縣。平遙城內有古縣衙,但目前縣人民政府位於古陶鎮(城外吧?)。古城只是平遙(地名)的一部份,平遙(地名)更只是平遙縣的一小部份。古城外的平遙,其潦草與大同、(木塔外的)應縣並無差異。
古城牆周長 6 公里多,若視為正方形,則城內面積不到 3 平方公里,至今卻還生活著幾萬人。城外的發展,我猜是始於閻錫山修同蒲鐵路時。之後,人口的增長應又迫使一些人住到城外。「連續停電兩三天」這件事應足以顯示平遙一帶民生基本建設的低劣(積極發展觀光業數年之後仍然如此,之前境況不想可知),因此住城內、城外或許並無差異,但仍好奇目前當地較富裕的人家會選擇住在哪裡。
原本以為古城裡都是明清民居、沒有「現代建築」,第二天傍晚吧,走到城的西北角(?),看到一片新建民居,才恍然不是這麼回事。後來回想,其實第一天下午走過南大街南端時就看到了一家鋼筋水泥建築的電影院(已停業),之後又在城南看到一家鋼筋水泥建築的中國人民銀行(亦已停業)。